「少数派报告」清洗与妥协: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1944—45(二)
「少数派报告」清洗与妥协: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1944—45(一)
《Cleansing and Compromise: The Estonian SSR in 1944-1945》
作者:塔尔图大学奥拉夫·默尔特斯曼(Olaf Mertelsmann);艾吉·拉希塔姆(Aigi Rahi-Tamm)
前情提要:本文的目的是分析苏联在1944-1945年间对重新夺回的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采取的两种政策方法:清洗与妥协。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有充分的理由阐述清洗和镇压的各个方面;然而,妥协政策的可能往往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要了解战后短期的情况,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镇压的规模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夸大。
苏联在后方的准备
被疏散到后方的爱沙尼亚人面临着恶劣的生活条件,但在劳动营中的爱沙尼亚士兵的情况肯定更糟。由于战争的缘故,他们的居住、工作条件和食物供应准备不足。只够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食物配给、恶劣的工作环境、衣物或住所条件不足、饥饿、过度劳累和寒冷造成了严重的减员。大约三分之一被疏散到后方的爱沙尼亚男性在六个月内死亡。【31】 在1941年至1942年的冬天,幸存者得以离开劳动营,恢复供应并被编入新的战斗部队,尤其是爱沙尼亚步兵军,或者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被派往后方工作。
收复爱沙尼亚的准备工作最开始很缓慢,但开始得很早。比如疏散到后方的爱沙尼亚艺术家聚集在雅罗斯拉夫尔组成艺术团体。1942年2月至1944年2月,最初在莫斯科,之后在列宁格勒,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努力召集党的工作人员,准备对爱沙尼亚展开宣传工作,配合那里的苏联游击队—但未能成功—并重新安排爱沙尼亚的战后秩序。【32】1943年,准备工作的速度加快。爱沙尼亚党组织在爱沙尼亚士兵和疏散人员中吸纳党员,开设专门课程为解放后的爱沙尼亚培养拖拉机手、书记员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
在战争胜利之后,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将按照苏联模式建立。除此之外,爱沙尼亚党还从“老共和国”(即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招募爱沙尼亚族,为了在他们“历史悠久的祖国”工作。早在1943年12月,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会大约有400名干部,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大约有170名干部,此时距离解放爱沙尼亚还有9个月。然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干部数量严重不足,无法在解放后履行必要的职责。必须开办新的培训班,招募更多干部。【33】
苏联方面对未来清洗的准备工作给予了特别关注。在这些镇压中档案将发挥重要作用。1940年,爱沙尼亚档案管理部门归属内务人民委员会。时任爱沙尼亚国家档案馆馆长的戈特利布·内伊(Gottlieb Ney)对档案从属于内务人民委员会表示惊讶,而内务人民委员会中央档案局(Glavnoe Arkhivnoe Upravlenie NKVD SSSR,简称 GAU)负责人福明的回答是,把档案馆作为研究机构的普遍观点应该很快被遗忘,在资本主义世界可能如此,但“在苏维埃国家,档案的主要任务是揭露阶级敌人,以便将其消灭”。【34】
1940年10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卡累利阿、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管理部门受命对“反革命分子”进行登记。这是一年前也就是1939年9月建立的全联盟“有政治色彩分子”档案库制度的延续。1941年春天,“有政治色彩分子”档案已经在爱沙尼亚登记了37794人。【35】战争爆发后相关档案的编制在苏联后方的基洛夫继续进行,爱沙尼亚国家档案馆特别部门的材料已被疏散到后方,同时还有大约53000人的身份信息补充进来。
1944年2月至8月,爱沙尼亚档案馆负责人伯恩哈德·魏默(Bernhard Veimer)留在列宁格勒,研究德国占领期间在爱沙尼亚出版的报纸,以便从中搜寻“反苏分子”。他的目标不仅是政治人物、警察或曾在德军服役的军人,还包括经济学家、农民、神职人员、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报纸记者等。1944 年7月7日,魏默将遴选后的文件提供给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县级内务部-国家安全部负责人,然后他们制定了特别名单。【36】
1944年,在准备收复爱沙尼亚时,中央档案局一再提醒魏默,要求档案馆必须向安全机关和锄奸总局提供其保管的机密资料,并帮助他们开展工作。【37】1944年秋天,该单位提供了大约16万份档案,用于苏联相关单位在行动中使用。这些个人档案是德国人在1941年至1944年间编制的,并在他们撤退后被遗留在爱沙尼亚。这些档案主要包括那些曾在德国军队服役、在前线阵亡、受伤或失踪的爱沙尼亚公民的数据。
1944年10月之后,苏联在塔林的安全机关继续整理文件。到1945年归档了45000多份档案。主要重点是搜索在德国占领期间运转的各种机构的材料。档案部门必须为行动部门提供有关这些机构编制体制的必要信息。【38】同时,档案部门收集了有关原“自卫团”成员和原德军部队军人的材料,或者关于失踪和被俘军人的材料。主要关注点是具体个人的政治忠诚,此外所有在审讯时作为证人被询问的人也都被登记在案。
苏联在大后方准备并培训了三个行动大队,以便在解放之后重建爱沙尼亚的苏维埃政权。他们的行动将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别行动人员进行协调。【39】 这些行动大队在1944年夏末红军进攻后立即开始行动。当时这些工作组主要执行以下任务:搜捕通德分子、叛徒、敌方特工以及反苏分子;清理德军残余和间谍小组;消灭反苏游击队;针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波罗的海境外活动组织的反情报活动。【40】这些行动大队与红军一起进入波罗的海三国,负责登记当地人口、保管档案文件和甄别人员。【41】
清洗与妥协
在1944年9月苏联重新夺回爱沙尼亚时,这里的人口比战前减少了四分之一。根据统计部门的估计,1945年1月1日,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居住着85.4万人,比30年代后期减少了28万人。人口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939年至1941年间,总共有2万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移民,不过其中有部分人并不是德意志族。当德国军队入侵时,由于苏联的疏散、大规模驱逐、动员和逮捕,人口已经减少了10万人。德国人杀害了大约8000人,3万人在战争中丧生,7000瑞典族移居瑞典,超过7万名爱沙尼亚族逃往国外。少数人被掳掠到德国成为“东方劳工”( Ostarbeiter),这部分主要是俄罗斯族。自1940年以来,爱沙尼亚人口一直在减少。此外,苏联的人口数据不包括士兵、战俘和其他囚犯,因此爱沙尼亚当时的实际人口可能要更多。【42】
接下来的几年里爱沙尼亚人口开始回升,来源包括被流放的爱沙尼亚人从俄罗斯回归、被从德国遣返并通过甄别营回国的人口、【43】复员的士兵、被释放的战俘和劳动营成员,以及来自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大量移民。第一次种族清洗发生在1945年夏天。爱沙尼亚仅存的大约400名德意志族公民,包括自愿跟随的非德意志族家庭成员被驱逐出境。【44】共和国境内共64名外国公民都受到了严格审查,并制定了一份特别名单,保证只有德意志族被驱逐出境。【45】
针对芬兰族、伊乔利亚族和卡累利阿族的第二波种族清洗发生在1946-1947年。【46】这些民族由于和爱沙尼亚人在语言、宗教等习俗方面接近,同时为了躲避迫害,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从卡累利阿苏维埃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移居爱沙尼亚。这些人通常要在24小时内离开爱沙尼亚前往俄罗斯内陆,他们的护照上盖有“§58-1”的印记,意思是“叛徒”。
随着重新占领波罗的海三国,克里姆林宫方面的注意力一度集中在“波罗的海问题”上。关于波罗的海三国党组织,联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了有关1944年10月底至11月初期间该各国党组织工作中的“错误和缺陷”的决议。这些文件成为在波罗的海三国推进苏维埃化进程的决议性文件,并影响了未来几年苏联在这些地方的政策。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波罗的海三国的主要问题之一。【47】
波罗的海三国党组织都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设立了特别机构(联共中央爱沙尼亚局、立陶宛局和拉脱维亚局),用以加强管理、打通信息往来渠道、推进苏维埃化政策的实施并清除“敌对分子”。【48】显然在1944年夏末和秋天,斯大林控制住了局势,并于1944年8月亲自会见了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党委第一书记。后来,具体的工作委派给安德烈·日丹诺夫、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分管,【49】斯大林则居中掌握,随时了解各局的活动。
早在红军还未重返波罗的海国家时大后方就已经开始制定重建的经济计划,但显然这样的计划要遵循苏联的总体框架。被毁坏的基础设施——发电站或桥梁——必须首先重建。然后大力发展重工业和能源产业。至于重建住房、粮食生产和消费品生产在经济重建计划中只能往后排了,这也是为什么战后爱沙尼亚人口恢复的速度如此之慢。实际上,由于苏联其他地区的饥荒和农业政策的影响,1946-1947年爱沙尼亚的粮食供应和营养标准比战争期间更差。【50】
经济转型、战后重建加上肃清“敌对分子”的措施交织在一起,尤其是第二次土改(1944-1947)政策。例如,塔尔图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埃德加·图努里斯特(Edgar Tõnurist)在1945 年1月宣布,仅在他的县就有800多“人民的敌人”和“通敌分子”的农场规模缩小到5-7公顷。图努里斯特抱怨说:“在乡村与敌人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展开。”【51】
党组织向农村派遣全权代表,与积极分子一起搜捕“积极的通敌分子”,通常是会召开公开大会。【52】总共有属于9000户家庭的123000公顷土地被没收。【53】当然,也有像某位季克同志那样的看法,他认为“通敌分子”被纵容,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54】许多家庭后来成为1949年大规模驱逐的受害者。被驱逐的20600人中有三分之二是“通敌分子”,属于“人民公敌”的范畴。1945年9月,苏联政府下令没收那些户主与德国人一起逃亡或家庭成员参加武装反苏游击战的家庭的房屋、农具、牲畜和个人财产。【55】
红军解放波罗的海国家之后,各行动大队开始展开活动。以奥托·蒂夫为首的爱沙尼亚临时政府成员及相关人员被捕。1944年10月,塔林开始了一场清洗行动,196人被捕。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命令所有相关机构移交德国占领时期的文件,以方便搜捕潜伏的敌对分子。1944年12月,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必须更换所有公民护照,从而对整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进行筛查。直到1946年初,在对护照持有人进行彻底甄别后,总共发放了28万本新护照。1945年1月,爱沙尼亚监狱中已有4200人在押。【56】
1944年4月,仍在列宁格勒的爱沙尼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重新建立由党员和共青团员、当地积极分子以及党和安全机关人员组成的歼击营的决定。它们在1944年至1945年间在解放的领土上成立,歼击营总部由爱共第一书记尼古拉·卡罗塔姆本人亲自领导。【57】歼击营在1945年1月1日有1653名成员,一年后有5804名成员。【58】歼击营官兵是“自愿”加入且无偿的,他们在反游击战中作为民兵组织,配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辅助单位。最初,苏联使用专门的安全部队围剿游击队。但遭受挫折之后改变了战术,1945年开始苏联更倾向于使用歼击营。他们的军事价值实际上很小,成员往往纪律水平低下,有些人像许多其他士兵和安全部队成员一样参与盗窃、抢劫并恐吓当地居民。【59】
1945年5月上旬,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给斯大林提交的一部分报告中,罗列了该党当前主要政治事务的排序:
爱沙尼亚党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清理共和国内部的敌对分子,加强地方党和国家机关,教育干部,恢复经济,进行农业改革和改善民众的政治教育:
1. 肃清共和国境内潜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敌对分子
正如此前的汇报,大批爱沙尼亚军事—法西斯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的大量积极参与者未能逃往德国、瑞典或芬兰……
根据这份报告,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4月,共有8909人因政治原因被捕。文中提到对逃进森林里躲避征兵的人进行特赦。在向苏联征兵办公室报到的爱沙尼亚士兵中,那些曾在德国军队服役的士兵被送往劳动营或建筑营服役。【60】重要的是,尽管报告强调了清洗的优先性,但它也揭示了妥协政策的要素,即进行大赦。
根据由莱奥伊斯普(Leo Õispuu)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关于1944年至1945年间不完全统计数据,至少发生了13700次政治逮捕,占斯大林主义在波罗的海国家十年统治时期总数的37%。共有381起死刑被记录在案,2600名被捕者未能幸免。从1946年到1953年,由于1947年5月至1950年1月期间暂时取消了死刑判决,与1940年至1941年的1874起死刑相比,仅登记了178起死刑。【61】因此,战后的清洗并没有之前对爱沙尼亚精英的毁灭那么残酷。尽管如此,逮捕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据关于民众情绪的报告中记载,人们在公开会议上询问这些逮捕的情况。【62】
苏联安全部门在曾在德军服役的爱沙尼亚军人中寻找被指控的和真正的通敌者和战犯,这些军人往往在战俘营或劳改营、甄别营或在苏联军队中服役。根据1943年10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的指令,所有曾在德军服役的波罗的海国家军人至少必须经过甄别,犯下战争罪行的士兵和军官必须被逮捕。【63】 例如,位于波尔库拉(Põllküla)的锄奸总局第0316特别甄别营中,在1945年11月22日之前,总共羁押了15937人,其中13340人曾经是军人。苏军士兵如果开小差跑到德军那边,通常的判罚是在特殊定居点强制劳动六年。显然有数千爱沙尼亚人受到类似的惩处。【64】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结论,有相当数量曾在德军服役的爱沙尼亚人没有经过任何甄别,直接进入红军部队、劳动营或建筑营服役,他们中有一些人后来被揪了出来受到惩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越来越多。在1944年12月上旬的爱沙尼亚共产党第五次全体代表大会上,已经对任何所谓爱沙尼亚特殊的论调发出了警告。随后开始逮捕爱沙尼亚知识分子。【65】
爱沙尼亚第一书记尼古拉·卡罗塔姆在1945年春天向当地干部解释逮捕风潮:“当有人被捕时,必须解释逮捕行动的必要性,说明这是人民的请求。我们收到匿名信,有时有签名,有时没有签名,控诉某个村庄的某些敌对分子是如何的猖狂。”【66】 当然,确实有民众抱怨,但展开清洗行动的主要倡议来自克里姆林宫,没有档案证据证明逮捕行动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事实上,爱沙尼亚苏联当局鼓励告发敌对分子,并在报纸上发表了相应的文章。爱沙尼亚人民委员会在1945年6月17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了地方政府应如何处理投诉和举报,必须及时登记并在三天之内展开调查。在苏维埃政权中,在显眼的地方要设置专门的举报箱,配备纸和铅笔。【67】
除了“通敌分子”之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匪徒”(反苏游击队)、“人民公敌”以及“旧政权分子”都受到怀疑并被从重要的岗位上免职。例如,贸易人民委员汉森和副人民委员约吉提出的建议被爱共中央委员会驳回,因为他们允许太多原商店店主或餐馆老板在社会主义贸易体系中工作。爱共中央认为“旧政权分子”对因酗酒、欺诈、贪污和腐败造成的所有商贸问题负责。【68】
(未完待续)
【31】Urmas Usai, ed., Eestlasedtööpataljonides 1941-1942. Mälestusi ja dokumente. Esimene raamat [Estonians in Labour Battalions 1941-1942. Memories and Documents. FirstBook](爱沙尼亚人在劳动营1941-1942 回忆与档案,第一版)(Tallinn: Olion, 1993), 5-18.
【32】Olaf Kuuli, Sotsialistid jakommunistid Eestis 1917-1991 [Socialists and Communists in Estonia 1917-1991](爱沙尼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917-1991) (Tallinn: O.Kuuli, 1999), 88-89; Olev Liivik, “Keskkomitee [Central Committee],” in Enn Tarvel, ed., Eestimaa Kommunistliku Partei Keskkomitee organisatsioonilinestruktuur 1940-1991 [The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the Estonian Communist Party] (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架构)(Tallinn: Kistler-Ritso Eesti Sihtasutus, 2002), 35.
【33】1943年12月24日和28日召开了爱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ERAF 1-4-97,85-86.
【34】Gottlieb Ney, “Teadlasest tshekistiks [From Scientist to Chekist],”in Richard Maasing, ed.,Eesti riik ja rahvas Teises maailmasõjas.Punane aasta [The Estonian State andNa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Red Year], vol. 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爱沙尼亚国家和民族红色年代,第三卷)(Stockholm: EMP, 1956), 154.
【35】Svodnyi ochet otdela sekretnykh fondov, 25 December 1942, ERAFR1490-1-1, 13; Margus Lääne, Valdur Ohmann, “Kuidas komprat koguti? NKGBinfoallikad 1941 aastast osaliselt säilinud operatiivandmete põhjal [HowKompromat was collected?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of NKGB in 1941 on the Basisof partly preserved Operation Data],”(如何收集黑材料?1941年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基于部分保存的行动数据的信息来源) Tuna 10, 4 (2007): 86-88.
【36】伯恩哈德·魏默提交给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会锄奸总局局长尼基京斯基和爱沙尼亚内务人民委员亚历山大·雷谢夫的报告,“Dokladnaia zapiska o prodelannoi rabote za vremia moego prebyvaniiav Leningrade ot 4/II do 25/VII”, 27 July 1944, ERAF 17/1-1-7, 38.
【37】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会锄奸总局副局长古里安诺夫给魏默的信,ERA (Eesti Riigiarhiiv — Estonian State Archives), R-2338-1-34, 94.
【38】“Plan raboty Arkhivnogo Otdela NKVD ESSR,” 24 January 1945, ERAR-2338-1-59, 3.
【39】Tõnu Tannberg, “Hilisstalinistlik Eesti NSV [The late StalinistEstonian SSR],(斯大林主义晚期的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 Eesti ajalugu VI , 273.
【40】爱沙尼亚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鲍里斯·库姆(Boris Kumm)给爱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Dokladnaiazapiska o rabote organov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Estonskoi SSR za period1940-1941 gg. i 1944-1948 gg.,” ERAF 1-47-37, 143-144.
【41】 Kuusk, Nõukogude võimulahingud… , 29
【49】Zubkova, Pribaltika i Kreml´…, 141-145.
【50】Mertelsmann, Der stalinistische Umbau…, 93-99.
【51】共和国农业专家会议速记记录,1945年1月17日-19日, ERAF 1-4-239, 3.
【52】 Feest, “Terror und Gewalt…,”, 663.
【53】Valner Krinal, Otto Karma, Herbert Ligi, Feliks Sauks, Eesti NSVmajandusajalugu[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stonian SSR]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史)(Tallinn: Valgus, 1979), 182.
【54】爱沙尼亚农业会议议定书,1944年10月22日-23日,ERAF 1-4-128, 94.
【55】Aigi Rahi, 1949, aasta märtsiküüditamine Tartu linnas ja maakonnas[The March Deportation 1949 in the Town and County of Tartu](1949年在塔尔图各镇、县的三月驱逐行动)(Tartu: Kleio, 1998), 26.
【56】Tannberg, “Hilisstalinistlik Eesti NSV,” 275.
【57】Tiit Noormets, Valdur Ohmann, “Saateks [Introduction],” in TiitNoormets, Valdur Ohmann, ed., Hävitajad. Nõukogude hävituspataljonid Eestis1944-1954. Dokumentide kogumik [Destroyers. Soviet Destroyer Battalions inEstonia 1944-1954.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破坏者:苏联歼击营在爱沙尼亚1944-1954 文件汇编) (Tallinn:Riigiarhiiv, 2006), 16-19.
【58】Statiev, Social Conflict and Counterinsurgency…, 221.
【59】 Lembit Raid, “Kas peremees või käsualune? Ülevaade Parteiarhiivimaterjalidest II [Master or Subordinate? Overview of Materials fromthe Party Archives II],”(主管还是下属?政党档案材料总览) Kleio, no. 8 (1993): 42-43.
【60】爱共中央政治局活动报告,1945年1月1日到5月1日,RGASPI (Rossiisko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social´no-politicheskoiistorii), f. 598, op. 1, d. 2,l. 2-6.
【61】Õispuu, ed., Political Arrests, vol. 2, D5.实际逮捕的人数显然要多一些。同一个团队确定1944年至1952年间25000名政治犯被捕,而赫鲁晓夫的一份报告指出同一时有45000人被捕(Zubkova, Pribaltika i Kreml´..., 332)。赫鲁晓夫的数字可能还包括普通刑事犯罪罪行。Aleksandr Diukov估计1944-1945年有10000人被捕,这个数字绝对太低估了,见于AleksandrDiukov, Mif o genocide: Repressii sovetskikh vlastei v Estonii (1940-1953) [TheGenocide Myth: Repression of Soviet Power in Estonia (1940-1953)](种族灭绝神话:苏联政权在爱沙尼亚的镇压(1940—1953)) (M.: Aleksei Iakovlev, 2007), 89.
【62】For example Svodka no. 4, 12 July 1945, ERAF 1-3-115, 14.
【63】“Sovmestnaia direktiva NKVD SSSR i NKGB SSSR No. 494/94,” Diukov,Mif o genocide…, 121-123.
【64】Erich Kaup, “Sõjavangilaagrid Eestis 1944-1949 [POW Camps in Estonia1944-1949](在爱沙尼亚的战俘营1944—1949),” Kleio: Ajalooajakiri 2 (1995): 34-35.
【65】 Feest, “Terror und Gewalt…,” 664.
【66】ERAF 1-4-245, 26.
【67】该法令曾被公布。Rahi, 1949, aasta märtsiküüditamine…, 32.
【68】爱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议定书,1945年6月7日,ERAF 1-4-
189, 33-35.
与本文内容相关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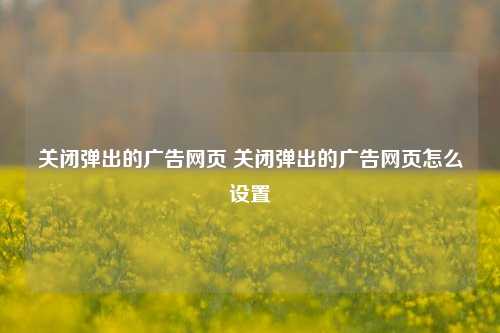



0 留言